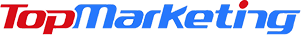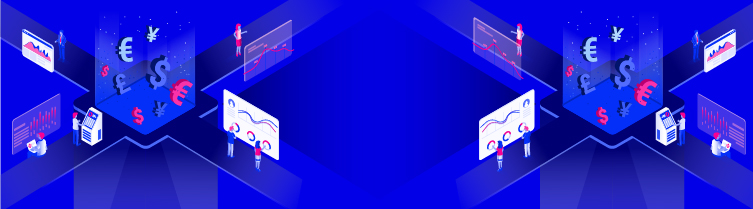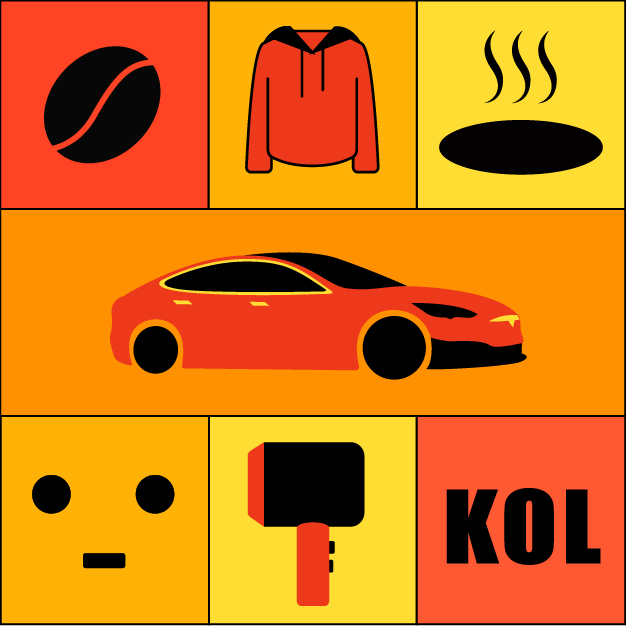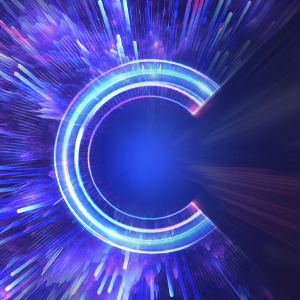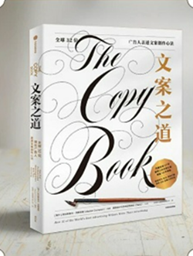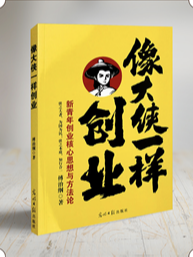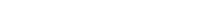音乐先声
音乐先声一觉醒来,发行24年的“《离别的车站》屠榜了:N版歌名、花样变调,各种版本挤爆车站,排队上车。
最近,音乐人董昱昆的吐槽“华语乐坛已经玩完”的视频在业内引发关注。他发现,在某音乐平台榜单前列出现了《来生别再相遇》《想你一次落一粒沙》《来生再和你相爱》等多首高度雷同的歌曲。
就像有人开了一条流水线,源源不断地把《离别的车站》加工成“新歌”,名字五花八门,旋律却如出一辙。
据董昱昆统计,在榜单前十位中,“《离别的车站》们”占据四席,TOP500榜单中更是有十余首不同的版本。其中,由烟嗓船长演唱的《来生别再相遇》连续在榜33天,最高排名稳居NO.1。
据董昱昆统计,在榜单前十位中,“《离别的车站》们”占据四席,TOP500榜单中更是有十余首不同的版本。其中,由烟嗓船长演唱的《来生别再相遇》连续在榜33天,最高排名稳居NO.1,堪称“车站VIP舱常客”。
一曲N唱,一唱就上榜。仿佛整个榜单都变成了《离别的车站》的候车大厅,每个版本都在争抢VIP座位。
然而,流量的快车早就超载了。
榜单成了“赛博鬼打墙”
按图索骥,我们先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检索了这位“烟嗓船长”。
截至9月9日,在酷狗音乐,他发布了938首单曲、674张专辑,1726.6万月听众;在QQ音乐,则有1708首单曲、673张专辑;在酷我音乐,发布了1713首单曲、667张专辑;在网易云音乐,发布了1048首单曲、439张专辑.其中,最早的一张单曲专辑发行于2024年3月。
即便以单曲数量最少的酷狗平台的数据计算,从去年3月11日到今天一共557天,发布了938首歌,平均每天发布约1.68首,非常之高产。
歌手主页显示,这位音乐人在总共有33首歌曲曾经登上过酷狗音乐TOP500榜单,其中热度的最高的当属这首《来生别再相遇》。在歌曲大火后,他顺势把《来生别再相遇》的第一句歌曲“孟婆她用眼泪熬成汤”创作成另一首新歌《我向孟婆求碗汤》,毫无意外,旋律仍是《离别的车站》。
当我们耐心地听完这33首歌曲以后,其中有17首都是对《离别的车站》进行重新填词,占比超过50%,歌名更是来生、今生、早点、晚点、相遇、遇见、遇到等几个词的排列组合;剩下的16首歌曲中,还有10首是基于《怨苍天变了心》旋律的重新填词。
值得一提的是,《离别的车站》和《怨苍天变了心》两首歌的作曲都是徐嘉良,且歌词页注明了为“正版授权填词作品”。也就是说,不同于此前的侵权洗歌,现在版权生意的音乐公司开始规范化了,会提前获取词曲授权,然后再开足马力,组团翻唱冲榜。
我们也注意到,榜单成绩最高的《来生别再相遇》还参与到了平台的音乐扶持计划中,利用平台在作品宣发、版权管理、渠道变现的资源倾斜,持续扩大传播声量。换句话说,即便一首歌只不过无限翻唱、批量试水的结果,但只要数据有了水花,就能在算法助推下反复推送到用户面前。
更为荒唐的是,伴随着电视剧《生万物》的大火,这首《来生别再相遇》在短视频平台上摇身一变成了《生万物》主题曲。各种用户自制的MV带上#生万物、#一部剧带火一首歌等话题,动辄就斩获上万的点赞收藏。
如果只是简单复制,恐怕还达不到最大化收益的目的。于是,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多版本蹭流量,更规模化、效率更高。
DJ默涵版、DJ豪大大版、DJ浩然版、伴奏版……同一个制作班底,换上一名女歌手,又发行了女版、DJ默涵女版,同一首旋律在不同平台反复上榜,用户感觉自己像在重复刷同一首歌,却不断点开新的链接。
此外,在《离别的车站》的旋律被证明有流量后,更多重新填词的作品也随之上架,重复一遍相同的打法。
例如,在同一家OP授权下,一位叫大潞的音乐人共有13首歌在TOP500榜单上,发布了8个版本的《离别的车站》,分别是《想你一次落一粒沙》以及姊妹篇《想你一次起一阵风》,绕不开前世今生的《下辈子再陪你永恒》等等。
当我们换个平台检索《来生别再相遇》时,又瞬时出现数百首挂羊头卖狗肉的歌曲,名字相同,却是粗制滥造的另一首歌。
在流量游戏里,这首《来生别再相遇》刚刚发行了1个月,无数个版本便扎堆涌现,而熟悉的旋律本身就是“现金流”,微调是手段,而算法就是点钞机。
只有听众,困在了音乐榜单的“赛博鬼打墙”里。
“一曲N唱”背后的流量逻辑
采买词曲授权,重新填词演唱,这在音乐行业中并不是新鲜事。
众所周知,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由于本土原创力量跟不上,港台音乐公司就曾大量翻唱了大量日本音乐人的曲子。那时,日本音乐工业成熟,流行音乐往往经过专业团队打磨,旋律结构、和声编配成熟,拿到优质的曲版权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市场的保证。
然而,在那个旋律大量“外采”的年代,真正的竞争力往往落在了歌词上。也是在那个年代,港台涌现出一批大师级作词人。例如,林夕、林振强、黄霑……让那些买来的曲子不再只是“舶来品”,而是被重新定义为港乐黄金年代的集体记忆。
但当下,“一曲N唱”的操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,他们挖掘国人熟悉的经典旋律,拿到版权授权后,粗制滥造地改编出几十个版本,势要榨取版权上的每一滴价值。“《离别的车站》们”能在榜单上迅速攻城略地,除了令人咋舌的手速外,也折射出一套当下热门的作词逻辑——短剧式作词。
就像短剧的数据跑通了重生梗、天龙人梗以及二婚嫁给京城首富梗后,层出不穷的故事都会套进这个模板中。“一曲N唱”的逻辑也如出一辙,歌词就像是流水线上的剧本改写:换个意象就是“再见旧人”,换个时态就是“未曾遇见”,换个意境就能瞬间升级为“爱到山海都枯竭”。
然而,算法喜欢这种“短剧式作词”——直白、浓烈、可预测,更容易触发用户的快速点击和反复收听。而播放量、完播率、收藏量、评论数、分享数等量化指标又决定了歌曲的排名。最终呈现出来的,榜单成为旋律复制工厂最醒目的宣传位,而热度也因此被进一步放大,就是鬼打墙般的音乐榜单。
当榜单或者歌单中的歌能带来实打实的流量时,平台的态度也会变得暧昧。
2025年1月,期刊《Harper's Magazine》就撰文披露了Spotify的“Perfect Fit Content”计划。据悉,这一计划开始于2017年,Spotify与多个供应商合作,供应商以极低的价格为Spotify提供多种类型的音乐,并且这些音乐的版权也永久转让给平台。随后,Spotify会制造幽灵音乐人来发行这些歌曲,并整合到那些收听量颇高的榜单上。
为什么?原因很简单。
Spotify每年需要向版权方支付巨额版税,而榜单或者歌单上的音乐并非用户主动检索。与其让Ed Sheeran的歌曲霸占歌单、支付高额版税,倒不如制造一批幽灵音乐人,花小钱生产旋律简单、版权可控的音乐,再大面积推送到歌单和用户面前。
这样一来,Spotify既满足了用户需求,又节省了大量版权成本,还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在互联网的运营逻辑下,一旦尝到了“偷常禁果”的甜头,纯靠自我约束,不是不可能,但很难很难。
对于认真做音乐的人和公司来说,这无疑是一场飞来横祸。
原创需要付出心血,承担风险,而“一曲N唱”的作品则前有熟悉的旋律做担保,中有N个版本实现规模经济,后有榜单上无数个版本作风险对冲。同质化改编可以快速制造情绪、跑通算法逻辑,平台的推荐机制就会天然向这些作品倾斜;而那些真正独立、需要听众慢慢咀嚼的原创作品,却在算法的黑箱里沉没。
原创的风险不仅在于投入产出比悬殊,更在于整个行业环境对“低质复用”的默许,逐渐挤压了原创者的生存空间。
久而久之,原创音乐人要么被迫妥协、加入“作词工厂”的流水线,要么在理想与生存之间艰难抉择。最终留下的,并不是最能代表时代审美的作品,而是最能迎合算法胃口的“快消品”。
这才是最让人感到讽刺和悲哀的地方。
结语
北岛说,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
原创音乐人费尽心思打磨每一句旋律、推敲每一行歌词,却常常败给那些旋律外采、歌词烂俗的快餐作品。平台表面上拥抱原创,但粗制滥造的同质化改编,却利用算法漏洞得以生生不息,赚得真金白银。
在“破窗效应”下,无底线的翻唱狂欢必然肆意泛滥,慢慢榨干根基本就薄弱的华语乐坛。
但长远来看,这样打破底线、竭泽而渔的音乐生态,还能支撑多久?
算法驱动下,“一曲N唱”规模化的爆发力虽然让平台用最低成本维持了最高活跃度,但一旦原创者被劣币驱逐、集体流失,音乐行业无异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本。
不用等AI下场,这个行业自己就会凋零,陷入真正的寒冬。
别忘了,那首最初走进人心的《离别的车站》,绝不可能诞生在这样的生态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