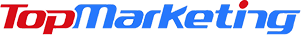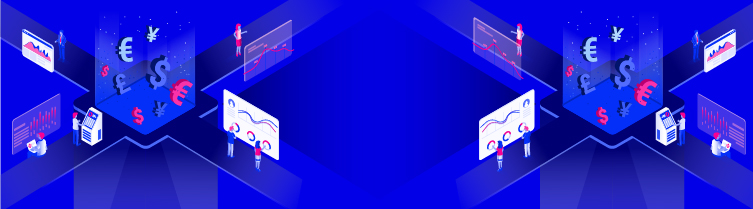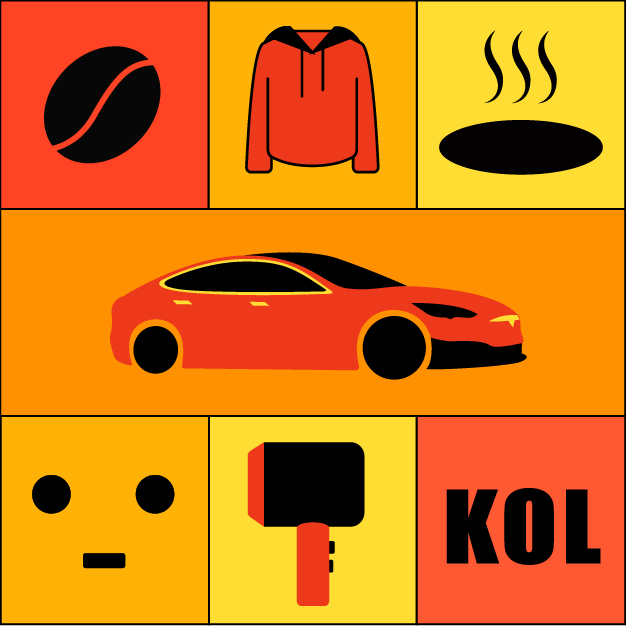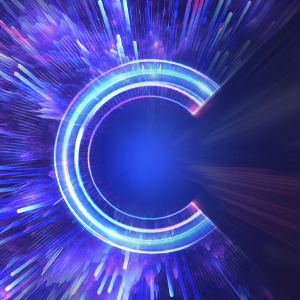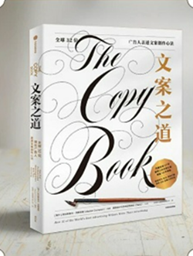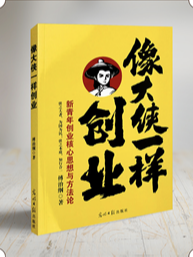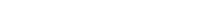剧风营
剧风营2025 年暑期档,动画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以 10亿票房刷新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纪录,登顶国产二维动画票房冠军。这部由《中国奇谭》短片衍生而来的长片,不仅有让人梦回80年代的中式动画审美的精致画风,更通过“小妖取经”的荒诞故事让无数打工牛马共情。除此之外,它以“用短片撬动长片”的制片模式也给行业带来很多启示。

图片来自:豆瓣
作为一个短剧自媒体,剧风仔认为,短剧也许可以以其短平快,成为大IP孵化的战略支点。投资一部上亿的电影、电视剧风险很高,但是如何能用几十万的短剧试试水,也许对两个行业都是好事。
创新模式,“用短片撬动长片”
《浪浪山小妖怪》里的小猪妖并非第一次跟观众见面。
它和其他几个长片中出现的角色最早出现在 2023 年《中国奇谭》第一集《小妖怪的夏天》中。《中国奇谭》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(以下简称上美影)主导,除了根正苗红外,还带着独属于上美影的气质。
不过在这一系列短片中,上美影的角色发生了变化,它不再是制作者,而是一个组织者、把关人。围绕“中国奇谭”的核心主题,上美影邀请十余个独立工作室展开自由命题创作。这些“小妖怪”般的外部团队,虽非上美影体制内成员,却带着在市场中磨砺出的对当代观众情绪的精准洞察 —— 比如《小妖怪的夏天》中“打工人被压榨”的剧情,正是源于对年轻人职场焦虑的捕捉。

图片来自:豆瓣
《中国奇谭》中最成功的就是第一集《小妖怪的夏天》,当时单集播放量破亿。结尾那句“我想离开浪浪山”,成了当年的爆款台词,各种二创剪辑刷屏。然而,并不是因为反馈坚定了制作团队制作长片的信心。实际上据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总策划、制片人崔威在接受采访时坦言:“一开始就想用短片撬动长片”。当她和监制陈廖宇、导演於水看中《小妖怪的夏天》的延展潜力后,便策划长短两部动画同时构思和创作。
在《中国奇谭》前期分镜制作完成后,《浪浪山小妖怪》便进入剧本创作环节。当《中国奇谭》完成画面制作时,长片的制作和前期也已经准备充分了。
这种双管齐下的制作模式打破了传统动画电影的生产流程。一方面,《小妖怪的夏天》可以被视为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的效果测试,前者的市场效果预示了后者的市场可能性。
另一方面,短片制作也培养了一个可以为长片生产助力的团队,而这大大缩短了动画电影制作的周期。“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生产周期之短之顺利,在国内二维动画项目中都是少见的”。
短片播出后,观众对“打工人隐喻”“社恐猩猩”等元素的热议,促使长片强化了职场生存、身份认同等现实议题的表达。导演於水透露,猩猩怪 “我是齐天大圣”的高光时刻,正是基于短片评论区“希望看到弱者逆袭”的呼声设计。

图片来自:豆瓣
短剧成为长片“战略前置”
《浪浪山》的模式创新,给了短剧行业新的启发,这种启发也许会重构短剧的行业生态位。
拍短剧可以不只是因为预算有限,且短剧回本快,也许短剧可以成为长片生态的“战略前置”。
在传统长片开发中,剧本、人设、风格的试错成本高达千万级。而《中国奇谭》仅用单集百万级成本,便完成了“小妖叙事”“现实隐喻”“水墨现代转译”三大核心方向的验证。
相较于《大圣归来》《哪吒》依赖经典IP改编,《中国奇谭》通过短剧集原创“浪浪山”符号。这种“短平快”的IP塑造方式,可以让《浪浪山》长片上映之前就获得一定群众基础。而长片对 “无名之辈价值”的哲学升华,反哺了短片 IP 的文化厚度;而短片中“社恐猩猩”的喜剧人设,为长片提供了天然的观众情感锚点。这种“短长互文”的叙事策略,大大增强了IP厚度。

图片来自:豆瓣
传统模式下,长片美术团队 70% 的精力消耗在基础设定上。《浪浪山》通过短片完成人设、世界观等“重资产”开发后,长片团队可将更多资源投入剧情深化。这种“以战代训”的机制,使《浪浪山》团队在操刀成片时更加从容,也提升了制作效率。
《浪浪山》这种模式或许可以平移到长剧生产中,一些大IP或者原创IP,可以先通过短剧试水,收集观众反馈,再做电影或者长剧。
通过短剧先行策略,制作方能够降低投资风险,用较小的投入测试市场反应,再决定是否加大投资力度。还能通过短片播出后的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,精准把握用户偏好。最重要的是,短片可以构建IP影响力基础。通过短片阶段积累的粉丝和口碑,会成为长片的潜在观众群。

图片来自:豆瓣
结 语
一直以来,短剧很成功,但是在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位很低,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的破圈,也许可以让短剧行业迎来一次价值重塑:短剧不再仅仅是廉价的碎片化娱乐产品,而是可以成为IP孵化的前沿阵地和内容创新的试验田。
如同《浪浪山》一样,也许制作公司可通过短剧降低长片风险,平台可通过短剧提升用户粘性,观众则能通过短剧获得更丰富的叙事体验。